iWeekly
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Nuri Bilge Ceylan)的新片《枯草》(About Dry Grasses)将在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上映。锡兰曾在柏林电影节、法国凯撒电影奖上获得多项荣誉。有人说他是游离在电影界的“孤狼”,用一套独特的电影语言坚守着最原始的艺术创作。他的作品都很长。“我知道,有时候看这么长的电影很难,但这个时代的节奏不适合我的灵魂,所以我拍的是一种对它的强烈抗议。”锡兰说,“幸运的是,仍然有人对这类电影感兴趣。当然,他们是少数,但我能做什么呢?这是我的节奏。”

女人在寒风中回望镜头,发丝随风飘起,挂满雪花,背后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静谧中释出几分落寞——在戏剧性的自然背景下呈现人物,这是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Nuri Bilge Ceylan)标志性的风格。今年,锡兰带着酝酿多年的新作《枯草》回归,锁定戛纳主竞赛单元,《枯草》讲述一个小镇教师在结束义务服务之后,希望被分配到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故事,通过一位安纳托利亚偏远地区的教师,审视边缘社会和孤独感带来的内在影响。
安纳托利亚当地人是锡兰作品的核心。安纳托利亚又名小亚细亚,是亚洲西南部的半岛,位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也是锡兰成长的地方。从第一部短片《茧》(Koza)开始,过去九部作品中,他专注于这片土地上孤独的人们。他创作的半自传体三部曲,包括《小镇》(Kasaba)、《五月碧云天》(Mayis Sikintisi )和《远方》(Uzak),电影中那些树林与田野的连接相交,变幻的晨曦暮霭、沉默的炉子、交错的山峦、稀疏散落的房屋、遥远的人……都反映着他童年的早期印象。
小镇青年的诗意“乡愁”
锡兰出生在1959年的伊斯坦布尔,在恰纳卡莱省的耶尼杰长大。耶尼杰是他父亲的故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城镇,价值观、真理和错误泾渭分明。锡兰的父亲是一名农业工程师,是那个地区唯一一个上过学的人,也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带着改造故乡的执念回到耶尼杰。随着时间的推移,锡兰目睹了父亲的理想主义在官僚主义的摧残下,慢慢成为失望,最后让位于幻灭。在锡兰读完小学四年级后,他们一家搬回了伊斯坦布尔。他们过着贫穷的生活。他曾说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冒烟的炉子,它让母亲得了咽炎,每当她咳嗽,他就会记起那些日子。

艺术并没有出现在锡兰的童年里。直到他15岁时,邻居送给他一本关于摄影的书作为生日礼物,火花才被点燃。他开始拍照,喜欢在暗室里呆上几个小时。高中毕业后,锡兰入读了博阿齐奇大学(Boğaziçi)的电气工程学,博阿齐奇前身为1863年成立的罗伯特学院,是美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一所美式高等教育机构。锡兰已经不记得自己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专业,他只记得当时的他对西方“有一种向往和钦佩,博阿齐奇大学把人们引向西方的一面,你会完成学业,然后去西方生活,我的命运在西方”。
这样的向往在几年后破灭。锡兰在大学学习电气工程,但梦想成为《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毕业后,他在伦敦一边做洗碗工,一边看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和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的电影,继续追求自己的激情。他身无分文,经常偷东西吃,直到有一次被一个男孩抓住,他第一次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耻辱感触动了内心。他说:“西方的价值观逐渐开始以不符合我灵魂的方式出现。”锡兰感到非常孤独,人际关系变得非常困难,他开始觉得和西方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直到他偶然看到一本关于喜马拉雅的书,他将它理解为来自东方的承诺和希望。他飞往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上走了400公里,坐在一座佛教寺庙的山顶上,看着群山,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很想念土耳其,于是决定回去。
回到土耳其后,锡兰去服了兵役。在那段时间里,他遇到了来自土耳其社会各个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我又产生了对祖国的爱,我找到了属于我的地方”。在军队的日子很孤独,但那恰恰也是锡兰思考、看电影和读书最多的时期。他读到了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发现了“相似的灵魂,和我一样的人,有和我一样的问题”。在他之后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能看到契诃夫的影子。“我读了很多书,其中一本书(罗曼·波兰斯基传记)让我想到要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为了存钱,锡兰在伊斯坦布尔担任商业摄影师,他的作品包括在阿拉拉特山附近的乡村男孩、下雨天的渡轮船长、黄昏的乡村道路、冬天的伊斯坦布尔金角,以及走在街道上的行人——他将广阔的风景与孤独的主角形成对比,这也预示着锡兰作为电影制作人的风格。

▲锡兰与妻子。
终于,锡兰赚够了钱买了一台Arriflex电影摄影机。1995年,36岁的他完成了第一部作品《茧》。这部短片以他的家乡为背景,他的父母担任主演。田野、树林里游荡的镜头,配合巴赫(Johann SebastianBach)的音乐,锡兰通过镜头讲述了小镇生活的无聊。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被邀请在戛纳展示这部电影,这是戛纳电影节上土耳其电影界的第一部短片。在之后的作品《小镇》中,锡兰刻画了一个失业、渴望在别处生活的年轻人;《野梨树》(The Wild Pear Tree)讲述的则是一个想成为作家,却处处碰壁的年轻人。或许是父亲理想主义的瓦解、或许是自己对西方向往的幻灭,这类小镇的失意青年是他早期电影的核心,那是土耳其一代人的乡愁和困境。这些电影戏剧化了锡兰与家乡之间错综复杂的不安关系,他是小镇中的一员,同时又是敏锐的观察者。
克制的反抗与挑战
土耳其电影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896年土耳其人就开始接触电影。经历了兴衰浮沉之后,在锡兰成为电影制作人的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电影几乎死亡,1993年在土耳其上映的154部电影中,只有11部是国内制作的。锡兰的出现,让土耳其电影在国际上再次有了姓名——《远方》获得戛纳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三只猴子》(Three Monkeys)赢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小亚细亚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natolia)赢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远方》剧照。
2014年,锡兰凭借《冬眠》(Winter’s Sleep)再次杀回戛纳,拿下金棕榈,《金融时报》评价:“这部精彩影片中,什么都没发生,但一切都发生了。”锡兰在获奖感言中说,“我想把这个奖献给我热爱的孤独而美丽的国家”,第二天,一张锡兰举起右拳的照片出现在土耳其各大报纸的头版。这一举动被广泛解读为是对土耳其导演尤马兹·古尼(Yilmaz Güney)的致敬。“我不介意这样的联想,”锡兰后来说,“我很喜欢《自由之路》(The Way),我看了很多他的作品。”

▲2014年,锡兰在法国戛纳电影节。
尤马兹·古尼被认为是土耳其民族电影的先锋和奠基人,习惯以尖锐的态度表现社会困境。1980年政变后,土耳其政府禁止发行所有古尼的电影。但他在监狱里继续写剧本,并在其他导演的帮助下完成了《自由之路》的拍摄。这部作品通过对军事统治下的土耳其的现实写照,捕捉到了这个国家的绝望。1982年,《自由之路》获得了戛纳的肯定,他将金棕榈奖献给了土耳其军政府的受害者,在领奖时举起了右拳。与古尼相比,锡兰的政治是沉默和克制的。在锡兰的电影中,政治作为背景噪音渗透进作品里。在《五月碧云天》和《野梨树》中,土耳其总理的声音从电视里传出,但主人公并没有对内容发表任何评论。《努里·比格·锡兰的电影》一书的作者认为,他的电影中缺少对话,在对风景的细致观察中展示小镇上的土耳其人如何在孤独中避难,同时见证了土耳其的专制现代化。例如在《野梨树》中,故事的主线是想要成为作家的司南回到家乡筹集出版费用,但在此过程中他看到了虚假的民主、政府的腐败,锡兰通过电影人物的映射侧面反映了时局下的土耳其政治现状——在2016年军方政变失败之后,数百名学者被解雇、流放或监禁,经济更是一蹶不振,购书者群体进一步萎缩,图书价格飙升,司南的写作梦变得遥不可及。
锡兰的作品不仅蕴含政治批判,作为现代土耳其故事讲述者,他也试图挑战西方对土耳其的看法。长期以来,土耳其的电影中,脱衣舞女、皇宫、海岸豪宅、监狱、蓝色清真寺等成为这个国家标志性的符号,吸引着西方电影人,土耳其导演有时会延续这些刻板印象。锡兰时常用轻松幽默的笔触处理对欧洲中心文化干预的不满。在《野梨树》中,司南在梦中躲在特洛伊木马中,这个道具正是为了拍摄德国导演沃尔夫冈·彼得森的电影《特洛伊》(Troy)而造的。影片拍摄完成后,道具被留在小镇里,既是礼物,也在提醒着人们好莱坞是怎样把这里当成垃圾场的。在另一个场景中,村长建议司南要在书中体现他的家乡恰纳卡莱“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并称“西方人对它感兴趣”。这种指导让司南感到沮丧,25年前,当锡兰开始成为一名电影制作人时,类似的建议也让他恼火。
他不仅挑战权力。有人说锡兰是游离在电影界的“孤狼”,用一套独特的电影语言坚守着最原始的艺术创作。他以摄影师的身份进入电影行业,以缓慢流动的镜头来说故事,画面中人物缓缓出现,缓缓消失,传递出一种疏离与落寞的感觉。他的电影很长,节奏缓慢,对白少、色调暗淡,《小亚细亚往事》时长157分钟;《冬眠》时长196分钟;《野梨树》188分钟;将于今年5月亮相的《枯草》则接近4小时。对于Netflix和TikTok的时代来说,看起来似乎有些笨拙。他在今年5月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说,自己拍电影之前“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不使用剧本,到片场之后我才决定要拍什么。”

▲ 锡兰(右)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
“人都是在变化,人的心境也在变化。有一个人,我之前和他有点矛盾,不是很喜欢他。但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他,却发现自己已经宽恕了,对他逐渐释怀了。电影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真实的生活感……在大银幕前,观众可以和电影建立更深的联系。”
“我知道,有时候看这么长的电影很难,但这个时代的节奏不适合我的灵魂,所以我拍的是一种对它的强烈抗议。”锡兰说,“幸运的是,仍然有人对这类电影感兴趣。当然,他们是少数,但我能做什么呢?这是我的节奏。”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撰文—朱怡
编辑—Y
图片—Getty、视觉中国、AF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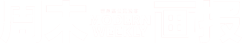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