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eekly
4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时隔6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城与它不确定的墙》发售。这是一次对于43年前“失败之作”的重塑,为发表但没有成书的同名中篇小说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符合村上给予自己的修补匠的定义,他不在乎自己是否做“诺贝尔永远的天才候选人”,他更关注写出来的文字是否遵从本心。

日本文学中火车总是一个重要的意象,若要查找相关分析必是繁博,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也曾因一段火车上的偶遇迁思回虑。那是很多年前去往东京的火车上,一名面容姣好的女性询问他是不是村上本尊,得到肯定回答后,女士自称是村上的书迷,并夸赞他的处女作,认为“那是最棒的一本”。聊到此时,村上心中已有预感,对方接着直言不讳道:“您一直在走下坡路。”作家常常需要面对各种声音,村上对于这样的批评并不意外,实际上,凭借处女作获得新人奖后,他的高中同学也对他嗤之以鼻,称“如果这么简单的东西都能成功,那我也可以”。新人作家时,村上会反省自己,但写作40余年,在审视自己作品、努力创作的过程中,村上也有了新的感悟。4月,他推出新作《城与它不确定的墙》,正是他走上文坛第二年发表过却自认失败的作品,揭开封存已久的故事,在重写中与过去的自己对话。
重写的乐趣
“就像一个‘详梦者’(dreamreader)在图书馆重读旧梦。”村上春树如此形容他创作新书的感受。始于2020年3月,新冠疫情之下,村上鲜少外出,这是一个审视内心的绝佳环境,抽屉深处的旧作也被他翻了出来。作为新作原型的中篇小说《城,与它不确定的墙》(两版标题以是否有标点符号作为区分)曾于1980年在《文学界》刊登,那是村上春树走上文坛的第二年,是在《1973年的弹子球》之后的创作,既没有收录在单行本中,也没有收录在文库,被粉丝戏称为“村上唯一被抹杀的小说”。村上回忆称:“当时我还不懂怎么写小说。也没有系统性地训练过写作,全凭感觉。所以那时能写的东西是有限的。”一如村上在解释他作品中的一些角色时说:“这个世界上总会发生奇怪的事。你不知道为什么,但它们确实发生了。”村上成为作家,大概就是这样,在人生道路上突然分出了一条岔路口。产生这个念头时,他还喝着啤酒在看棒球比赛,他清晰地记得当年比赛双方队伍的名称、第一棒人员是谁、打出的第一球是怎样,也很明确那个想要成为作家的想法填满了他的思绪。他在回忆录《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描述了那种感受:“好像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飘然落下,我准确无误地抓住了它。”

那时的他,已经叛逆了许久——经历了高考落榜,见证了学生运动,流连过酒吧,露宿过街头,也不顾父母反对在大学还没毕业时就与阳子步入婚姻住进了岳父家。夫妻二人日夜打工了3年,才以250万日元资金与250万日元银行贷款开了一间属于自家的爵士乐咖啡馆兼酒吧“彼得猫”(Peter Cat)——融合了村上钟爱的爵士乐与猫咪元素。确定要进军文坛后,村上看完球赛立刻买了钢笔和稿纸投身创作,他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就是在“彼得猫”的厨房写下的,每天打烊后写一至两小时,大约花了六个月时间完成了创作,一举赢得1979年群像新人奖,推动了他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专职写作后,村上夫妻卖掉了“彼得猫”,他的生活也变得简单,被写作、跑步与音乐填满。村上对音乐的喜爱有时会让他被妻子埋怨,因为上世纪90年代,村上家中就有3000张黑胶唱片,到2021年已经是上万的庞大数字。但在音乐中,他学到了很多关于写作的东西。韵律、协调和即兴是三个重要的元素,均是生于对音乐的感悟,与文学无关。“当我开始写作,我便试着像弹奏音乐一样书写”。音乐也成了他作品中的一部分,他最知名的作品《挪威的森林》,书名取自披头士同名歌曲。他在《海边的卡夫卡》中评价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在《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中评价舒伯特。那些留在他脑海里的节奏都是他精心收集的回忆,他总会为他们找到合适的居所。

▲村上春树书房中收藏的黑胶唱片。
村上的写作日常有自己的节奏与规矩,基本上凌晨四点左右就能自然醒,投入创作前,先放一张黑胶唱片,声音不会太大,10到15分钟后,他就会忘记音乐,专注写作。村上不喜欢设置截止期限,他认为写完便是完结,但他每日都会写上十页稿纸(每页400字),即使写到八页觉得写不下去了,也一定要完成十页的内容,这大概会花上五六个小时,接下来便是跑步。从1983年开始跑步以来,这已经被村上视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不认同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法国十九世纪现代派诗人,患有性病、长期服用鸦片)的不健康生活,他欣赏石黑一雄写作时全身心投入,不写作时周游世界的态度。村上表示,长时间的写作需要强健的身体。“我有时候会写一些非常不健康的东西,奇怪、扭曲。我觉得如果要写这样的东西,就必须非常健康。这是一个悖论,但确实如此。”村上在与《纽约客》的对谈中提到跑步对自己的意义。
村上将写作比作园艺,合适的遣词造句就像在正确的时间、地点把种子撒到土壤里,而村上创作时最喜欢的部分是重写。“写作很有趣,重写更有趣。”他每天开始写作的第一步就是修改前一天的内容,不会改得面目全非,但要改得更为流畅。他常常将自己想象成一个修补匠,“我必须成为一个完美的修补匠,我必须写出好句子——真诚、美丽、优雅,且有力”。在采访中,他常提到,妻子会提供重写意见。每当一部作品完成时,阳子就是村上的第一个读者,等她读完,手稿上大概会贴上200张便利贴,均是需要重写的部分,村上便着手修改。如此反复几次,便利贴也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不需要再重写时阳子也会帮他厘清,每当妻子做了这样的决定,村上都会顺从地答应。
《城,与它不确定的墙》的重写,并非第一次。1985年发行的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将城中的主人公与在东京的主人公所展开的冒险故事交织在一起讲述,但创作历程也十分不畅,2017年回想起来他仍感到很郁闷。这一郁结最终因《城与它不确定的墙》的完结画上了句号。提笔时,村上只是想改写失败的故事,但在写完第一部分后,他觉得故事应该继续下去,最终成稿为672页,从中篇变成了长篇。在第一部分中,17岁的主人公和中年的主人公两条故事线交替讲述,主人公17岁时交往的女生告诉他真正的他“存在于被高墙环绕的城里”,而中年的主人公恰恰就在那个城里,所以是应该留在墙内,还是到外面的世界?异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织是村上作品的一大特色,“墙”作为重要意象在他的小说中频繁出现,他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解读道:“有各种各样的墙,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墙,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墙,或者像柏林墙一样实体存在的墙。这部作品中出现的墙到底是什么?我也是一边思考着它的意义一边写下去。在全球化动荡的时代,俄乌冲突、英国脱欧,社交媒体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们是躲在墙内还是跨越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写的时候,也不清楚自己究竟被哪一边吸引。”

除了“墙”,另一个重要元素“影子”,也出现在了这部小说中,村上将“影子”视作潜意识的一部分,类似于他的消极面,通过它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但因为主体与影子之间的区别给写作带来了难度,重写便尤为重要,提及原因,他表示:“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写多少部小说。因此,我必须带着感情去写这个故事,并花足时间去做这件事。”
做文学的修补匠
距离村上春树上一次出书已有6年时间,但人们对他的期待依旧如常。《城与它不确定的墙》发售活动中,书店在巨大的LED屏上倒计时,书迷大排长队、端着咖啡彻夜品读,初版30万册在首周就卖出了超过一半。在日本,村上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被誉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书迷中年轻人尤其多。而在世界范围内,他的宏篇巨著《1Q84》在法国仅一周就卖出7万本。

▲4月12日深夜,等候村上春树新书发售的书迷在东京一家书店外排起了长队。
他还有另一个被人熟知的形象“诺贝尔文学奖永远的天才候选人”,每年诺奖前后村上都是网友最乐于参与讨论的话题,各国媒体对于他为何拿不了奖的分析文章也循环往复,重写了许多遍。村上的态度,在不同的渠道都有表达,有一次,他在和记者对谈前表示:“我对绅士小说家有个定义:第一,不谈他缴纳的所得税;第二,不讲自己的前任;第三,不考虑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请不要问我以上三件事。”在他的回忆录中,他也写道:“小说家这一职业,至少对我来说,无所谓胜负成败。书的销量、得奖与否、评论的好坏,这些或许能成为成功与否的标志,却不能说是本质问题。写出来的文字是否达到了自己设定的基准,这才至为重要。”至于作为作家,他是否想要取得怎样的成就,2014年接受《卫报》采访时他回答称:“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年轻时的偶像。但他在四十来岁就死了。我也喜欢卡波特(Truman Garcia Capote,代表作《蒂凡尼的早餐》),但他在五十来岁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我理想中的作家,他在59岁死了。我不知道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我80岁时,我会写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我在跑步和写作,那就很好了。”

▲2016年,得知村上春树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书迷愁眉不展。
写作40余年,村上还能回想起刚开始动笔时的生涩,但如同向下挖掘泉水,他也在写作的过程中变得更有雄心。新书发表后,他形容自己“具备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能力”。所以,有人认为他在走下坡路时,他会予以反驳,他认为自己写得越来越好,这是他40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在火车上遇到的女孩让他想到了爵士音乐家吉恩·奎尔(Gene Quill),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名非常有名的萨克斯乐手,深受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影响。有一次,他在纽约的爵士吧演出时,一名年轻人对他说:“嘿,你不过就是像查理·帕克一样在演奏而已。”对此,奎尔把他的乐器递向年轻人,“给,你来像查理·帕克一样吹吹看”。村上总结道:“这件轶事告诉我们三点:第一,批评他人很容易;第二,原创很难;第三,但总得有人去做。我做了40年,这是我的工作。如果有人苛责我,那我会拿出我的乐器然后对他说:‘给,你来试试!’”
撰文—汪柚希
编辑—金布莱
图片—Getty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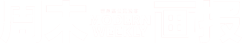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