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eekly
开胸手术需要将人的整个胸骨锯开。剖开回忆,安妮·埃尔诺只需要一段话:“在周末,我会做繁重的体力活,园艺或者打扫屋子。到了晚上,我筋疲力尽,四肢酸痛,仿佛和A相处了一整个下午。但在这种情况下,我所经历的疲劳是空洞的。没了另一个身体给我的记忆,这种疲劳让我厌恶。”
“临床手术般的敏锐”,诺贝尔文学奖组委会将埃尔诺的笔比作外科手术器具,它割开的是她的“痛苦、羞耻、屈辱、嫉妒与无法看清的自我”。10月,埃尔诺获颁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组委会在颁奖词中形容,埃尔诺“释放写作的力量,用不妥协、平实的语言展示人生”。宣布颁奖时,埃尔诺错过了通知电话,她当时正在自己的厨房里听收音机,“想知道今年的文学奖到底给了谁”,没想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就像你在沙漠里走着,天上突然来了一架飞机给你传信”。今年82岁的埃尔诺出版了超过20部作品,其中多数是自传体文学。她的作品以回忆录与虚构作品之间的无界限闻名。在她的笔下,女性的身体、记忆与生活不断被一刀刀割开。这些作品的主角面目模糊,因为她们可能是读者中的任何一个。

身为女人
“回忆大师”,《纽约时报》2020年时这样形容这个“在法语世界广为人知,在英语世界却一度令读者倍感陌生”的作家。埃尔诺观察生活中的一切。电视节目、明星绯闻、日用品商店、街上的行人与海报、她的父母与她自己的生活,她的疾病、情人与孩子。她爽朗温柔,获得诺贝尔奖后接受电话采访,首先是一阵笑,她轻声说“这太奇妙了”。疫情期间接受《纽约时报》的越洋采访,埃尔诺在电话里为记者形容自己所在的屋子,好让他有与自己面对面的感觉:“我坐在我的旧扶手椅上,房间里有扇形的窗户,我可以看到天空、云和树,这里非常安静。”
“应该如何形容埃尔诺?女人、小说家、写日记的人?她对自己充满羞耻的生活做了痛苦的调查,她是自传小说的大师,却没有同行们那种过度强调流派的懒惰。”《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杂志将埃尔诺的作品比作家庭老照片。翻开它们的瞬间,回忆扑面而来。“在她的写作中,没有什么是多余的。每件事都让人觉得很重要。”1940年,埃尔诺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童年“贫困但很有抱负”。她的姐姐在埃尔诺出生前就意外身故。父母经营咖啡馆和杂货店,埃尔诺在自己的纪录片中说,父母开的小店占据了自己全部的童年。“我与父母的生活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好像我们一直生活在顾客们的注视下……客人们看着我吃饭、写作业。”她渴望独处,过“一种孤独的生活”。中学时同班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同学,让她“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现在我到巴黎去,还有一种撬锁走进别人家的感觉。感觉我不属于那里,我是来自郊区的乡下姑娘”。

“年轻时,我承受的是不能分享的痛苦。”埃尔诺的父亲小学毕业就开始打工。父亲不能理解爱看杂书的妻子和翻阅波伏娃、伍尔夫的女儿,“我的父亲并不需要靠那些书来生活”。他有暴力倾向,曾殴打埃尔诺的母亲,几乎将她杀死。在1997年的作品《耻辱》(Shame)的第一句,埃尔诺提笔写下这个令她寒毛直竖的场景:“六月的一个星期天,我的父亲试图杀死我的母亲,时间是在下午。”
高中毕业后,埃尔诺在鲁昂大学与波尔多大学考取了教师资格证,也完成了文学学位。大学时她曾尝试写作,但手稿被出版商拒绝,理由是“太有野心了”。大学快毕业时,埃尔诺开始担心这是她在步入社会、结婚生子之前最后的一段自由时光,她不断询问自己“我该如何过自己的生活”,“我是否终有一日能到大城市的街道上漫步”。

在毕业后的几年中,埃尔诺还是走了一条“较多人走的路”。毕业后她找了一个教师职位,结了婚,生下两个孩子。直到30多岁时,埃尔诺才重新提起创作的勇气。丈夫菲利普在她第一次被出版社拒绝后嘲笑她的作家梦,埃尔诺瞒着丈夫,背着所有人写下自己日后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清除》(Cleaned Out)。《清除》讲述的正是她与父母和丈夫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手稿出版后,菲利普感到“委屈又愤怒”,他批评妻子“假装在写博士论文,其实只为独自创作不被打扰”。“菲利普对我说,如果我有能力写出一本书,我日后就有能力欺骗他。”两人很快选择离婚。这段破碎的婚姻与无法平衡“妻子”与“作家”双重身份的矛盾之后被埃尔诺记录在《一个冰冻的女人》(A Frozen Woman)中。埃尔诺在书中不仅剖析自己的婚姻生活,还回顾她生活中那些“拒绝顺从与社会的女人”,比如她那个顽强、不愿屈服于丈夫的母亲。埃尔诺之后再也没有结过婚,“与他人一起生活让我厌倦”。
1991年,在薄薄的一本《简单的激情》(A Simple Passion)中,埃尔诺回忆自己与一名外交官情人交往的细节。她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等待情人的电话,如何在情人离开后心如死灰,“与我交谈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对他们的谈话表露兴趣,这与他们的描述甚至话题本身无关,而是因为我遇到他之前,他曾在话题提及的地方生活”。《简单的激情》出版后,埃尔诺收到许多法语读者的来信:“男人和女人都向我倾诉。他们对我说,他们感觉自己才是写下这个故事的人。”在另一本小说《持有》(The Possession)中,埃尔诺毫不避讳地描写自己对旧情人找到更年轻新伴侣的嫉妒:“我所有的想法都落在她身上,这个女人填满了我的头脑、我的胸腔和我的肠胃。她总是与我在一起,她控制着我的情绪。”
 埃尔诺出版的作品。
埃尔诺出版的作品。
“我用一整页也无法描述清楚的事情,埃尔诺只要一句话就能写明白。”法国作家、哲学家迪迪埃·埃里本(Didier Eribon)评价。2019年,埃尔诺的作品《悠悠岁月》(The Years)被翻译成英语,出版后获得当年英语市场著名奖项国际布克奖提名。《悠悠岁月》回顾了她六十年的人生,离婚、孩子长大、父母病逝、她养的猫、她的伴侣们,其中穿插着披头士乐队、国际局势、法国文化与社会浪潮等大环境的变迁。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不写“我”如何,而是写“她”“他们”与“我们”。埃尔诺对英国《卫报》解释这种独特的写法:“当我想到我的生活,看到我从童年到今天的故事,我的故事与我们这代人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混在一起。在自传写作传统中,我们谈论的是自己,我们之外的事件只是背景。我想把这一点反过来。”她对《悠悠岁月》在意大利、德国等地受到读者欢迎“感到非常惊讶”:“通过我的感受与回忆来讲述这段集体历史,《悠悠岁月》的主角是时间与它的流逝,它带走一切,包括我们的生活。”2000年,埃尔诺到访中国,她对中文读者写信致意:“我最大的希望是《悠悠岁月》能使你们,中国朋友,接触一种法国人的记忆。一个法国女人的,也是与她同一代人所熟悉的记忆。”
 《正发生》改编的同名电影。
《正发生》改编的同名电影。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往往会将非出版专业的读者分为两类:读者要么从未听过获奖作者,要么只是‘隐约听说过’得奖人。有的作家有价值但有点沉闷。偶尔地,还会有作家将自己的影响力从地区性上升到全球性。”《纽约客》杂志写道。“安妮·埃尔诺就是这样的作家。她的作品有一种声音。它令人难忘,一旦读过就不容易忘记。不仅是其中公开或隐藏地捕捉时代的片段,还有句子的韵律与咒语般的文字。”埃尔诺是历史上第一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成立以来,全球只有另外16名女作家获得过这个荣誉。在颁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评论,埃尔诺的作品“有普遍意义,它能影响到每个人”。
无论国籍,在埃尔诺隐藏个体面貌的故事中,读者都能找到符合自己生活的一块碎片。《大西洋月刊》书评人奈莉·赫尔曼(Nellie Hermann)写道,埃尔诺的书是“对记忆、自我、写作力量和限制的挖掘”。《正发生》(Happening)讲述埃尔诺失去孩子的痛苦经历,《一个女孩的故事》(A Girl’s Story)回顾了她的性遭遇。“埃尔诺的书大部分很薄,许多都在100页以下;阅读这些书,你会看到一个女人真实、透明地希望找到理解自己的方法,通过这种理解与其他人联系起来。她叙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然后质疑自己的写作。她的作品有一种亲切感,部分来自于她对性、对父母的疾病与死亡、对自己与男人们之间卑微关系的坦诚。读者能在其中看到她的思想,她如何与世界互动。这种亲密关系的结果是,每个阅读她作品的人都觉得,她‘是我们的’,我们与她的关系是独特的。”
 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参加新闻发布会。
埃尔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参加新闻发布会。
《纽约时报》则提出,在私人回忆之外,埃尔诺的经历展现的是更普遍的妇女与工人阶级的生活,她的作品“捕捉到法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刻,她看到了法国从传统价值观转向更世俗、更开放的瞬间”。获奖后,今年82岁的埃尔诺对媒体承诺自己将继续写作:“获得诺贝尔奖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它恰好说明我要继续下去。作为一个女人,我认为妇女并没有真的实现平等。”2020年她曾在媒体采访中说,自己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失去向内看和回头的能力”。1980年代,埃尔诺看着母亲被阿尔茨海默病一点点吞噬。“我宁愿现在死掉,也不愿意失去我看到、听到过的一切。记忆对我来说是取之不尽的一片海。”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林湃
编辑:Y
图片:Getty、视觉中国
iWeekly周末画报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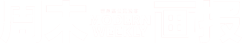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