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eekly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无论其获奖理由还是得奖感言,都给人一种非常介入社会正义之感,明显她是相信文以载道的“进步作家”。因此当我读到她最私密甚至离经叛道的作品《沉沦》的时候,我吃了一惊。
安妮·埃尔诺称她自己48岁的情欲日记含有“某种露骨、晦暗、直截了当的东西,类似祭品”——“祭品”二字相当扎眼,从一开始就为这本《沉沦》定下一个有点悲壮又有点残忍的调子。但如此艳情甚至充满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的戏剧性的一份祭品,是要献祭给谁?以什么为代价?又交换了什么呢?
 安妮·埃尔诺
安妮·埃尔诺
事发时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那年世界风起云涌,柏林围墙、东欧、苏联……如骨牌效应,而漩涡的侧边,巴黎,一个中年女作家与一个苏联驻法外交官陷入了一场胶着难分的孽恋,干得天昏地暗,不亚于外界的天翻地覆。
这未免让人想到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的名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安妮·埃尔诺和她的苏联情人岂不成就了一场意外的倾城之恋?正因为苏联在瓦解之前的混乱,这个多情的外交官才得以夜夜笙歌、流连在安妮的床笫之间,直到巨变前夕他才被召回,时间点恰恰好,安妮·埃尔诺有点骄傲地总结:“内心深处,最大的幸福将是个人爱情与历史洪流交错,苏联的改革演变(革命)促成我俩相逢,就像《飘》般的传奇。”
天哪,《飘》?她的自我定位比《倾城之恋》高得多。但没有卡夫卡超然——卡夫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当天,日记里只是写了寥寥的几个字:“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
 1984年,安妮·埃尔诺出版《一个男人的位置》。
1984年,安妮·埃尔诺出版《一个男人的位置》。
相对于《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和范柳原,安妮·埃尔诺和她的苏联情人S更像是法国版的张爱玲和胡兰成,考虑到S也许是克格勃特务出身,这一点更令我们吃惊——而更令安妮·埃尔诺痴迷。一方面是:爱欲令一个48岁的成熟女作家变成一个晕头小女孩,她急于献媚、自我怀疑、妒意中烧……就像张爱玲对胡兰成说:“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另一方面,欲望还是难免有隐晦目的。
有的人之欲发展到权力欲、掌控欲,那就成为了国之欲、时代之欲,如洪水滔滔。安妮·埃尔诺不在乎那些,但她的欲望被别的东西推波助澜,一样洪水滔滔。
那就是“苏联”作为一个审美对象,对那一代西方作家尤其是法国作家的魅力,这点从纪德、沙特、艾吕雅、阿拉贡一路下来,几乎成了一个传统。安妮·埃尔诺坦言:“我还知道因为他是苏联人所以我喜欢他。绝对的谜,有人会说是异国情调作祟。有何不可?我深深为他的 ‘俄国灵魂’着迷,或者可以说 ‘苏维埃精神’,苏联这整个国家,地理上、文化上(历史)感觉是如此的相近,然而却又是如此的迥然不同。”

“苏联”在书中出现68次(不算“苏俄”出现的7次),频率仅低于“做爱”这个词。但在安妮享受那位象征了俄罗斯之美的白皙高挑健壮美男子(我不禁想她也会爱上普京吗?)的高级性爱之余,她还是会被另一个苏联所困扰,“这篇关于苏联的文章让我痛不欲生”——那是她不想面对的现实的、被S效忠的那个斯大林遗物苏联。
面对强悍的S,安妮·埃尔诺也知道她的资本是什么,她渐渐懂得用自己老练的情欲经验、资本主义的精致消费、性解放时代残留的体位……这些来绑住一个比自己小一代的来自铁幕后保守国家的男人。但因此她也免不了俗气地贬损S的妻子、想象他还可能存在的别的婚外情,她几乎放弃了一个作家的高傲,虽然她还多次揣测S是因为她的作家名气而对她迷恋。
还是得请出比安妮清醒的张爱玲,姑奶奶在《色·戒》里提到:“通往女人心的路,是阴道。”反之亦然,如果阴道的满足成为了生命的全部,心不免会淤塞。做爱、等电话、做爱、等电话、做爱,如此翻来覆去的心身俱疲之余,安妮·埃尔诺偶尔,很偶尔想起自己是个作家,正在荒废文学。
 2022年10月6日,安妮·埃尔诺的著作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展出。
2022年10月6日,安妮·埃尔诺的著作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展出。
日后她才知道,这就是文学本身。那就是她决定把日记原封不动出版,不标注虚构还是非虚构的原因。这也让读者顿悟,为什么情欲常常以日记形式呈现为文学,如虚构的狄金森日记、普希金日记、慈禧情人的日记等。不可讳言,从读者角度看是为了迎合我们必有的窥淫癖;从作者角度看,是更为赤裸裸的自我解剖甚至自残,试想今天的安妮·埃尔诺看回那个神魂颠倒的痴情女人,除了冷眼审视,还是会有一份对她曾经恐惧老之将至所以乱了阵脚的心态的怜悯吧。
“我年青的时候,一度很渴望跳过即将来临的中年,直接进入老年。青春披挂的虚荣和欲望,在年轻时尚能以一股少年心气去掩饰过去,到了中年则尽显其丑陋峥嵘,而分外招人厌恶。老年因为寡欲,反而有一种赤条条无牵挂的率真——当然,前提是你需要先拥有智慧。”这是一个香港作家的看法。而安妮·埃尔诺的做法是,在老年来临之前放弃理性的计较,纵情于欲——前提是她在对的时代遇见对的人——哪怕在别人眼里是错的时代、错的人。
安妮·埃尔诺说:“阿根廷作家波赫士(Borges)的那句话好美: ‘世纪更迭,事件发生唯在当下;空中、地上、海上数不尽的人,真实的一切,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我很明白这些道理,而且了解得彻底通透。”这句话,完美地说服了我——为什么要享用《沉沦》这一祭品,经历这个女人用聪明的阴道和迷糊的头脑所体验的一年。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廖伟棠
编辑:喜乐
图片:GETTY
iWeekly周末画报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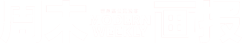




 © 202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2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