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eekly
如果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再多活几年,他恐怕不会对那个紧随而来的国际黑塞热潮感到多少欣慰。“在开始你们的LSD致幻剂实验之前,先读一读《悉达多》和《荒原狼》。”1963年,时任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这样告诉学生。利里致力于研究迷幻药对人的精神成长和治疗的作用,也是个黑塞迷,在杂志《迷幻药评论》(Psychedelic Review)上,他公开宣称黑塞的小说是指引迷幻药之旅的“无价指南”。尽管不久后他就因这种备受争议的研究和授课而被哈佛大学开除,但一场以迷幻药和嬉皮士为核心要素的反主流文化浪潮,伴随着“黑塞热”,很快汹涌而至。《悉达多》和《荒原狼》,这两部黑塞写于1920年代的小说被奉为反叛精神的圣经,黑塞本人也被视为新一代精神导师,更有一支直接以“荒原狼”命名的摇滚乐队在20世纪60年代末风靡一时。后来的几十年,黑塞成为20世纪最畅销的德国作家,也是仅次于格林兄弟和卡尔·马克思,作品翻译次数最多的德国作家。当然这一切,黑塞永远不会知道。他在1962年便去世了。

黑塞不会想到,“荒原狼”哈立·哈勒尔(Harry Haller)在魔剧院中看到的种种幻象,对无数混乱自我的剖析解构,在后世会被解读为一种药物作用下的迷幻。就黑塞本人而言,他一生从未碰过此类致幻剂药物,唯一的“毒品”是红酒。他也从未去过美国,不会说英语,甚至认定“日本人最了解我,而美国人最不了解我”。然而,正如德国《明镜》周刊在1968年所言,偏偏是美国的嬉皮士们,将这个已经日渐式微的作家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萧瑟”光景中拽了出来——在他生前,许多同时代的德国现代主义大家常常对他不屑一顾:表现主义诗人哥特弗雷德·贝恩(Gottfried Benn)称他是“一个小人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讥讽他“展现了通常比他伟大得多的作家才会有的缺点”;即便在大众当中,尽管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光环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德国作家”,但在那之后,人们对他的印象似乎也渐渐淡去,到他离世之时,德国《时代周报》公然在讣告中宣布黑塞已经“过时”。如此高居于文学正殿,又如此不合时宜。
但黑塞一定毋宁不合时宜,也不要当那一群嬉皮士的精神领袖、青年人的启蒙老师。他对于自己的作品总是在青少年当中交口流传感到不安:“看到中小学生们在那里如痴如醉地阅读《荒原狼》,我就会油然一股无名之火。毕竟,事实上这本书是我在50岁生日前不久才写的。”哪怕是他的第一部小说、27岁那年写出来的《彼得·卡门青》,当它被当时的德国青年流行团体“漂鸟运动”(Wandervogel)引为典范,激励一大批追随者像卡门青那样从世界和社会返归自然的时候,黑塞就已经流露出了相当的不满,厉声指责人们完全误解了卡门青:“他绝不想走许多人已经走烂了的路,而是要坚决地犁他自己的小径。他并非为集体生活而生。”可以说这也是黑塞自己的写照。终其一生,黑塞都在努力保持真实,尤其是在面临被排斥或被同化的外界巨大压力下,努力保持真实与自我,“如果我在我过往的写作中回溯一条意义的共同主线,那么我确实能找到一条,那就是对人性、对个体的辩护——有时甚至是绝望的辩护”,临终之前,他这样写道。
 1970年,摇滚乐队“荒原狼”。
1970年,摇滚乐队“荒原狼”。
在自我“神话”中求索
严格来说,“误读”黑塞并非年轻人的错。如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亚当·基尔希(Adam Kirsch)指出,黑塞笔下的主人公们之所以吸引年轻人,是因为他们确有那种人们在青春期才拥有,而到成年后遗忘或摒弃的热烈情感:伤痛、激荡,抑或是对生活的无限渴求。无论是生活在印度佛陀时代的悉达多,德国爵士乐时期的哈立·哈勒尔,还是中世纪的歌尔德蒙(《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他们始终以青年人的意气风发,试图在一个没有容身之所的社会里挑战既有秩序。只是在黑塞这里,向外的热情与放浪形骸最终要化为向内的自省与求索。在《德米安》中,叙事主人公辛克莱以一种完全真诚、严肃的口吻袒露他探究自我命运的心路历程:“我曾经是,现在也仍是一个求索者,但我已经不再质疑星星和书籍。我开始聆听血脉对我低语的教诲。我的故事并不愉快,不像虚构的故事那样甜蜜或和谐,它有着荒谬和混乱的味道,癫狂和梦想的气息——就像所有不再自欺欺人者的生活那样。”
荒谬和混乱,癫狂和梦想,这是黑塞自己的青春物语。1877年,他出生于德国西南部风景秀美的施瓦本山林中,一个颇具宗教历史的小镇卡尔夫,父母双方都来自虔敬派家庭——作为德国新教的一个教派分支,和英国的卫理公会一样,虔敬派成员敬虔事奉,支持一种热切地向内、福音派式的美德追求,也强调教育机构要强化宗教教育,以期培养出虔敬而智慧的“善良基督教徒”。这种虔敬主义思想成为黑塞的家族信念。1891年,14岁的黑塞被送往莫尔布隆修道院,一所位于中世纪修道院内的精英公立寄宿学校,它致力于招募所属地区最聪明的男孩并将他们教化成路德教会的牧师。但黑塞天性不羁,与学院规训形成了尖锐冲突,他在翌年春天逃离莫尔布隆,被学校紧急报告“失踪”,却又在第二天自行返回。不久,他又流露出自杀的念头,感到难以应对的父母只好将他从学院接走,送去一个精神疗养所。面对着在疗养所里遥遥无期、可能终身被禁锢的前景,他给父母连番写信:“我打心底厌恶这里的一切。就好像它是专门为了给年轻人展示生活方方面面的悲惨而设计的。”几个月后,他终于获准离开,上了当地的一所普通高中。父母彻底放弃了让他皈依虔敬派、入职教会的愿望,他也渐渐走上了文学道路。

黑塞在第一部小说《彼得·卡门青》中的第一句话可能充满了对家庭出身和青春往事的喻指:“在生命的伊始,是有神话的。”这个神话既是卡尔夫的旖旎风光在年幼的黑塞心头种下的自然种子,更是修道院和精神疗养院经历给他投下的漫长阴影。或者说,是他为自己的不愉快过往精心设计的一个诠释性神话,在后来的无数故事里不断被复述:一个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主人公,在主流社会枯燥、平凡的期望中显得格格不入,他遇到了一个或多个智者,变得孤立,直至踏上自我发现的旅程,直面内心深处的冲突。讽刺的是,这种向内的、精神自传式的写作,也恰恰是黑塞一直努力逃避的虔敬主义主要的文学形式。他自己也说,“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写作方式,是一种作为忏悔的行为”。他反抗虔敬派的教养路径,却一生未曾丢弃早已养成的严格自省习惯,也从未失去过对神性体验的渴望。
虔敬主义也许部分地构成了黑塞的个人底色,但它远非全部。在写作生涯早期,黑塞就被自己的文学偶像歌德那种对内心生活的关注,以及浪漫主义对“灵魂的秘密源泉”的关注所吸引,也着迷于尼采和他的“超人”哲学,即认为人可以拥抱上帝之死,然后在一种纯粹的自我导向中茁壮成长。更深远的影响则发端于1916年,彼时已经举家迁居瑞士的黑塞认识了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很快对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产生兴趣。黑塞喜欢荣格对于童年时期形成的内在符号网的关注,以及后者的人格阴影理论,相信那些令人厌恶、想要隐藏的负面人格,只是成长过程中尚未充分激活和发展的功能,也是内在活生生的另一个自我。这在相当程度上加深了他自己的人生观:“我唯一的兴趣在于内部。”他宣称写作是“一条漫长、多变、曲折的道路,目标是表达作家 ‘自我’的个性”,直至那个自我“最终被解开,暴露无遗,洗劫一空,消耗殆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49岁那年,黑塞写下《荒原狼》,哈立·哈勒尔那个“不仅在身体和精神、圣人和罪人等两极之间摇摆,也在成千上万极点之间摇摆”的内在自我,俨然充满了荣格原型人格理论的色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似乎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黑塞的向内求索,尽管黑塞多半不知道《离骚》,也不知道屈原。但通过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人,他知道了比屈原更早的中国人:老子,并在老子的道家思想中看到了不同于西方精神分析学的另一种哲学,他所谓“生活的两极似乎在瞬间彼此相触”。在写给挚友、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书信中,他曾说,“老子多年来带给我极大的智慧和安慰, ‘道’这个字对我意味着全部的生活真谛”。他同时也对另一种东方哲学,兴趣颇丰:印度佛教,这要归功于他的父母都曾在印度传教的经历。等到1911年,34岁的黑塞亲身前往印度、斯里兰卡、缅甸等地游历。但和父母为了传播基督教而去的目的不同的是,他以求索者的身份前往。这段经历最终成为小说《悉达多》的主要灵感来源。《悉达多》重复了黑塞的早期神话原型:一个敏感而有天赋的年轻人(悉达多),拒斥着自己的家庭、宗教和家人对他的期待,踏上了一段发现自我的旅途。乍听之下,它很像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证悟成佛之前的故事,但黑塞却对它进行了巧妙的改写。小说的一个重头戏是悉达多遇到了佛祖本身(黑塞将真实的乔达摩·悉达多在小说中按姓名拆成二人,乔达摩代表已经证悟的佛祖,悉达多则是仍在求索的年轻人),却并不对后者毕恭毕敬,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宗教,即便再如何真实、受人推崇,都是自己开悟的障碍。“没有人会通过教义获得救赎!”悉达多大喊。黑塞“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宗教教义,既不激进也不传教,而是始终保持对其他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开放态度”,传记《黑塞:漂泊者和他的影子》(Hesse: The Wanderer and His Shadow)作者贡纳尔·德克尔(Gunnar Decker)这样解释。

强调向内的探索与自省,不过分关注外部世界,在那个风起云涌的20世纪上半叶欧洲,足够落人话柄。一战爆发之时,当交战国家的多数诗人和作家也迅速卷入彼此攻讦的文字战争时,黑塞却似乎对所有的民族主义情绪免疫。1914年11月,他在瑞士的《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上刊文呼吁人们克制,“爱比恨更伟大,理解比愤怒更伟大,和平比战争更高尚。这才是这场邪恶的世界战争应当烙进我们记忆的东西”,结果却让自己成为新一轮攻讦的中心,德国媒体轮番向他开炮,读者的仇恨邮件纷至沓来,许多老友也与他割席。同样的经历以另一种方式在二战时期再现。尽管他本能地反对希特勒与纳粹主义,也用自己位于瑞士蒙塔尼奥拉的小屋接待和帮助了许多流亡作家,包括他的反纳粹德国同胞——小说家托马斯·曼和戏剧家布莱希特等人,然而,黑塞本人却从未真正投身于反纳粹政治浪潮。和托马斯·曼的著作在1930年代初期就被纳粹焚毁不同,黑塞的作品直到1943年才被纳粹正式列入禁书名单。人们希望他能够采取更公开的立场反对纳粹,他却回答说,就对内在自我的背弃程度而言,反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样的:“它与我何干?我无法改变任何事情。我所能做的,只是为那些努力想要阻止纳粹以肮脏勾当追求权力与政治霸权的人们,提供些微的帮助。”在那之后,战争硝烟殆尽,他也彻底遁入瑞士的山林,在田园牧歌中遗世独立,直至生命尽头。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降b小调
编辑:北北
图片:Getty,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iWeekly周末画报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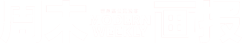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