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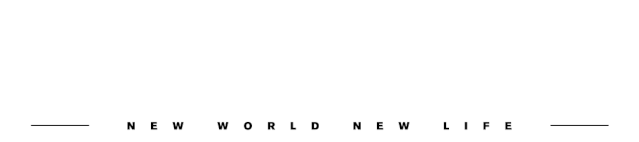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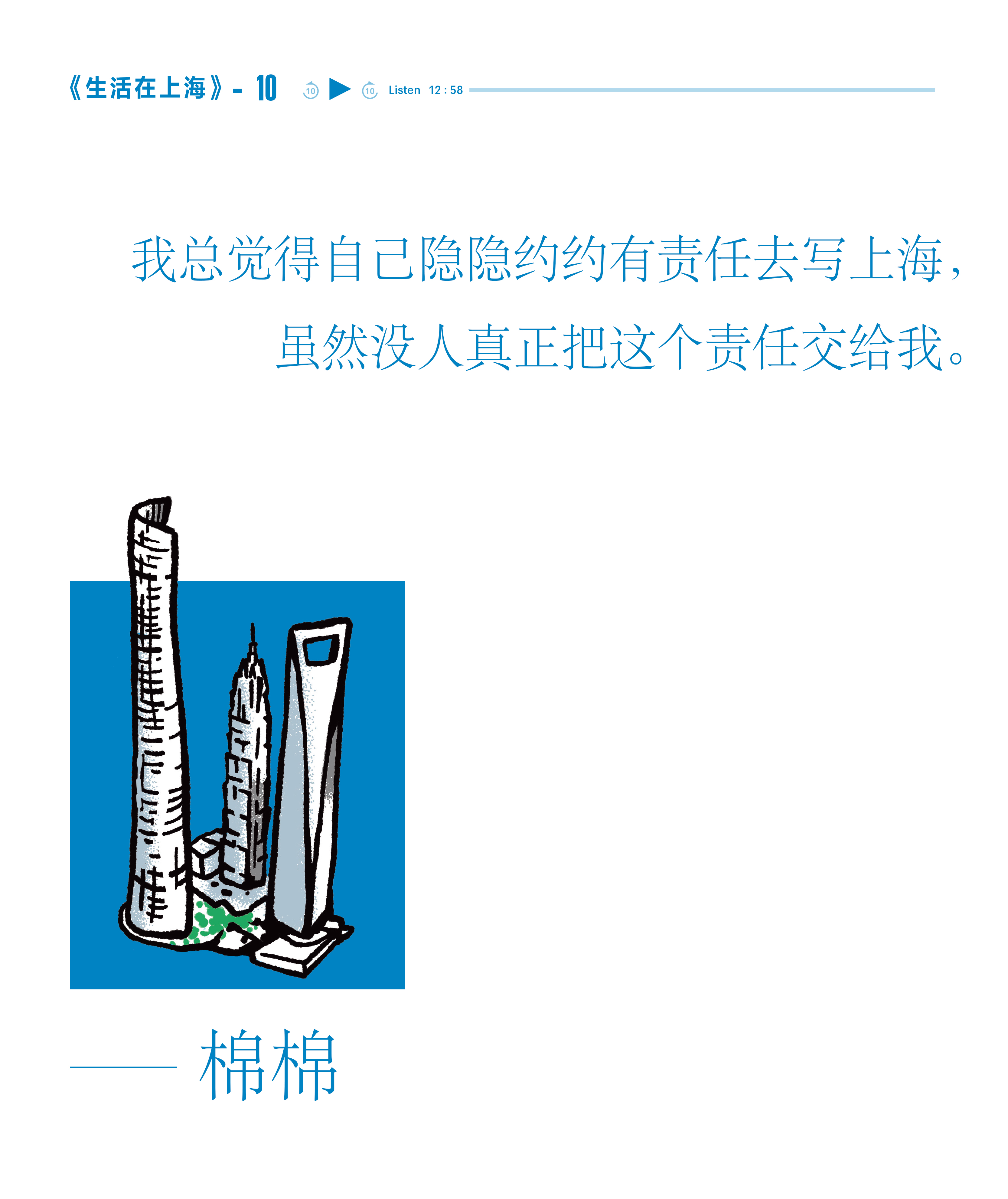
2000年左右,《上海文学》杂志社曾开设“城市地图”栏目,栏目策划者就是作家、《繁花》作者金宇澄。在当时,《上海文学》邀请不同作家展开一段段纸面上的city walk,二十年后,接续南方文艺复兴与city walk热潮,我们试图开展一种新的声音漫游,在iweekly app上线一档文化播客节目《生活在上海》。

![]()
《生活在上海》是由《生活月刊》和《上海文学》杂志社特别策划的文化类播客节目,这是用文学的方式进行的一次虚拟city walk。不局限于某个地标,而是一种更自由的文学行走,在上海这个城市的范围里,用作家们的经验、记忆和想象,串联起的一种行走。
![]()
|生活在上海 - 10|棉棉x木叶 x 崔欣:十四年后,再谈上海与写作
本期“生活在上海”荣幸邀请到《上海文学》执行主编崔欣、与作家棉棉、诗人木叶,展开一场关于文学、写作与上海独特气质的深度对话。2024年底,棉棉出版了新书《来自香海的女人》。 “香海”自然是这次讨论的话题。
棉棉与木叶的上一次见面,已是14年前。当时吴亮对木叶说道:“你应该去采访棉棉,棉棉已经是活化石了”。在这次重逢中,棉棉和木叶讲述了上海和北京带给他们的不同的体验。棉棉说,上海像一个女性,开放、柔软又包容,因此她用类似拼贴的方式去写作,把生活的碎片自由地拼接成故事。而北京在她眼中更像一个男性。木叶则坦言,自己既没有完全被北京人接纳,也未能真正融入上海,但正是这种游离,让他看到了上海的多层次面貌——“古代的,现代的,民国的,八九十年代的,怀旧的先锋,还有未来的,仿佛是从未来走来的上海。”
节目播出之前,棉棉说,这期标题可以叫“生活在香海”。可是,香海在哪里?她在书中写道“欢迎来到上海,香海是高度概念化的,就像‘我’是高度概念化的。来自香海的女人,尽管有着炙热的情感和情绪,但她们是非物质的”。木叶说,香海里的女人充满了声音,说起话来,像一首自我的变奏曲。用木叶的话来说,“比较香海的地方,相当于一个比较city的地方。”
这座城市,当然有她所生活的上海的影子。从街道名称到市井气息,从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交流,到城市独有的节奏与氛围,上海的一切都为作家提供了丰沛的灵感。棉棉感慨地说:“我总觉得自己隐隐约约有责任去写上海,虽然没人真正把这个责任交给我。”棉棉提到了她旅居加德满都的经历,但无论走多远,她发现自己写的始终是上海。在当代英语文学中,上海的形象仍是空白,而棉棉和她的同行正用文字打开一扇窗。
音频节目将在iweekly app“听闻”频道&小宇宙“听生活”频道上新。以下为部分精彩摘要。
【7:38】棉棉的作品是把很多东西重新编织过的
崔欣:棉棉每天要交500字的状态很像民国时期作家为报纸写专栏,编辑在厅外等稿,写完就立刻拿去排版。这种紧迫的创作氛围与棉棉新书中对专栏内容的重新编织和总结相呼应,不再是简单的一篇篇专栏。
【10:01】上海是“女性的”
木叶:《来自香海的女人》这个书名充满想象,“香”仿佛结合了香港和上海,也可能是结合了一种就国际化的元素。书中提到上海是“女性的”,是充满了各种各样声音。而棉棉的作品像在不断地变奏。《声名狼藉》里说上海最大特点就是“看不到大海”。但我发现还有一个下海,所以说上海这个城市它非常丰富。小说里真实与虚构交织,我觉得已经很难去完全去区分。
【13:04】棉棉创作是“量子文学”
木叶:棉棉创作是“量子文学”——真实与虚构交错,爱与恨纠缠,仿佛多重化身在故事中穿梭。又有点像印象派与表现主义的融合……就是各种各样的色彩,各种各样的声音,然后奔跑着向你涌来。
崔欣:小说仿佛可以无限延续,随时开始或停止,像读诗集一样,随便翻开一页都能感受到棉棉独特的表达。
【19:24】”香海“是复数的、古代的、现代的、未来的
木叶:我算是一个闯入者,既未被北京接受,也未完全融入上海。但我其实很关注上海。比如张爱玲的“到底是上海人”, 这句话的含义太丰富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它还是很浸染于生活中。孙甘露形容“外滩是上海的一个体外的心脏”,如今连接上海的身体和上海浦东的另外一个身体。这个”香海“是复数的、古代的、现代的、未来的。
【25:14】香海,很city的一个地方
木叶:梧桐树下,是现在上海比较奢华浮华和很city的地方。有一个外国的说法,越繁华的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也不过是“宇宙的郊区”。上海同样如此,既有绚烂夺目的盛宴,也有一些不为你所知和疼痛地方。棉棉描绘的是上海”响亮“和刺激的一面,而金宇澄、王安忆则展现了”不响“的一面。
【28:22】波兰像20年前的上海,而我不会再成为波兰夜生活的中心
棉棉:年轻时因刘索拉,许多新的作品展现新的生命觉知,这种觉知推动我去写东西。写作是始终是让我观察自己的一个手段。对我而言写作是我观察我自己,我搞定我自己。上海是我独特的题材,但我明白,在波兰,曾经的夜生活中心地位无法复制,因为那个时候在上海我真的是夜生活的中心,这种中心是很命运的。
【32:24】金宇澄的鼓励:“在长篇里过日子。”
棉棉:金宇澄年轻时时髦低调,他鼓励我写长篇:“要在长篇里过日子”。但我写作始终带着恐惧,出版困难让我无法完全放松。唯有写加德满都的乞丐时,我才能放下压力,观察生活的细节。
【37:28】我在观察加德满都但回到家还是在写上海
棉棉:加德满都街头修鞋匠被误认乞丐、唱歌跑掉的男乞丐以及盲眼女乞丐的快乐神情,让我想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可我又觉得与自己无关,还是更想写上海。这种游走正是我的写作方式。
【54:32】作为一个作家,我永远在观察
棉棉: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在国外,人家是不知道我是作家的。因朋友介绍,我住进意大利一个很美的小村。但是当我住了三年以后,我已经不再重要了,我从“上海作家”变成了一个村民。村庄的生活是很苦的,农民没有地,所以这些农民的孩子们其实都走了,那离开的孩子肯定跟这个村民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我作为一个作家,我永远在观察。
【56:57】对抗白人男子看亚洲女性的眼光
棉棉:站在国际视角去看,顾彬就是一个特别爱中国的汉学家。比如说顾斌说我的东西是垃圾,但是他看到我,我看到他,我们肯定很快就可以聊天。很多作家,他会觉得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怎么一下子就出名了。而我的小说The Lady from Shanghai就是为了对抗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白人男子看亚洲女性的眼光,
【01:07:25】 生活在一个“副本世界”,人际真实的接触格外珍贵
木叶:我就觉得我们现在那种生活,尤其是像棉棉这种多语言多维的生活,它是跳跃的,像在生活在一种副本的世界,在这种副本之中又不断变奏、再生,形成新的一个生活状态。如今,像Tiktok,让人仿佛生活在虚拟与真实交错的世界。说不清哪个是副本世界,哪个是原版世界。
棉棉:这正是这本书的核心,就像《威尼斯之死》一样,未曾接触的爱情却带来真实的情感冲击。在赛博空间里,真实与虚构更无界限,人际真实的接触才显得格外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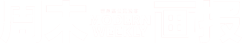




 © 202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2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