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eekly
杰拉尔德·穆南(Gerald Murnane)这个名字,对许多人来说都很陌生。中文世界,迄今没有一部穆南的著作翻译出版。借用《纽约时报》在四年前对他作出的评价,他是“大多数人从没听说过的最伟大在世英语作家”。看似矛盾,却恰如其分。1995年第一次宣布封笔的时候,他的第五部小说《翡翠蓝》(Emerald Blue)只卖出了600本;而当他在1999年获得帕特里克·怀特奖(Patrick White Award,以首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命名的文学奖)的时候,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已绝版。然而,作品的“少产”并不妨碍穆南获得许多同行后辈的高度认可,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PEN/Hemingway Award)得主、尼日利亚裔作家特朱·科尔(Teju Cole)甚至形容他是“天才”和“贝克特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他的名字也曾多次出现在博彩公司的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在他的小说中,人们看到一望无际的围场,也看到灵魂深处的神秘景观。”美国书评家达斯汀·伊林沃思(Dustin Illingworth)这样评价他的写作。
 杰拉尔德·穆南
杰拉尔德·穆南
纵是如此,穆南仍旧一次又一次地,想要从文学世界的繁文缛节中抽身,尽管也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在1995年的《翡翠蓝》之后,过了14年,他才以一部《大麦地》(Barley Patch)宣布归来,然后接连出版了《书的历史》(A History of Books,2012)、《百万窗户》(A Million Windows,2014)。2017年的《边境地区》(Border Districts)被他再次宣告为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但也再次“食言”了,他在疫情期间所写的文集《致读者的最后一封信》今年刚刚出版,当然,这本书从书名看就似乎是又一场宣告。不过,对于已经82岁的穆南来说,这一次可能是真的告别封笔了。
一个技术作家
穆南从很早就开始告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写作方式在如今的文学界不受欢迎。他的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也不强调人物塑造或历史背景的讨论,用英国小说家E·M·福斯特的话来说,他笔下的人物很不“丰满”。从第三部小说《平原》(The Plains,1982)开始,他小说的核心主题几乎就是一对孪生兄弟:阅读与写作。在《平原》中,身为电影制作人的叙述者来到一处平原,想要捕捉到平原居民的生活方式,并借此了解这片土地的意义。然而他却发现,无论是平原居民的言语还是思想,都无法通过电影的方式呈现:每个平原居民对这片平原风光的形状和意义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而每个平原居民生活的实质也不是任何其他人可以看到或听到的,只存在于过去的他们和现在的他们之间,那条时间的洪流中。最后,这个叙述者放下电影计划,一头扎进了图书馆,沉浸于那些讲述时间、讲述过去的满怀期待与现在的失望之间巨大落差的书中,那些其他人可能会称之为“小说”,但平原居民却称为“道德哲学”的书。

土耳其裔美国作家米尔维·埃姆雷(Merve Emre)认为,穆南的写作很容易让人想到俄罗斯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提出的“时空体”概念——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奇特融合,它创造并渗透了小说中看不见的景观,也塑造了所有生活于其中者的思想。而《平原》的“时空体”最终通向了叙述者在书纸间的探索和头脑中的思维,也抵达了穆南一直主张的观点:对“叙述者头脑中某些内容的叙述”才是“真正的小说”,因为它记录下的是叙述者所思考的“已经发生,或没有发生,或可能发生,或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不过,和许多作家不同的是,穆南笔下,叙述者的思考是以紧凑而高度完成的风格呈现的,既有别于法国意识流大师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那种时序颠倒的蒙太奇式写作,也有别于和他同时代的德国人W·G·泽巴尔德(W. G. Sebald)糅杂历史与记忆的沉重自省。穆南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技术作家”,宣称“唯一可用的主题是心理意象”,尤其重视通过语法和词汇的精确使用来彰明故事叙述者的思考。例如,“我,一个不喜欢 ‘想象’这词的人,更喜欢用 ‘猜测’这样的表述”,《百万窗户》中的叙述者这样介绍自己。

《书的历史》开头则是一段有些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描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对夫妻,站在一个城镇的主要广场上,这个城镇可能在50多年前,在《国家地理》杂志的一期或另一期所谓关于中美洲某个国家的文章中被描绘过。时间大概是下午三点左右,空气肯定很热。男人和女人在广场上争论了几件事,至少有一次,女人打了男人,男人也打了女人。”和穆南后期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这段描述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没有专有名词,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篇“所谓”的文章,还有“大概”“肯定”这样削弱陈述确定性的副词,一种既特殊又含混、既暴露又隐蔽的矛盾感跃然纸上,似乎生怕读者会将小说与现实生活的某种情形对号入座。就这一点来看,它和南非作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J.M. Coetzee)强调小说的虚构性,将国家浓缩成政治寓言、将人物浓缩成原型的创作理念十分相类。然而,到了《边境地区》,穆南这种以文字和语法来提醒读者小说之“虚构性”的手法则变得更加平铺直叙,“在写前一段的时候”“这一段后面的七段”“我在这一章的第四段写过”,这些通常只有在非虚构写作,尤其是论文写作中才会出现的用语,直白而突兀地从故事叙述者口中冒出。“我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报道一些看似虚构的事情。”故事的某一处,似乎对读者的怀疑了然于胸的叙述者会这样自我解释。

这也没错。缺乏情节的《边境地区》本质上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讲述60岁的叙述者如何抛下过往的生活,独自搬到一个偏远边境地区的小镇,打算在那里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自称是一个“失败”的读者,卖掉了几乎所有的藏书,想要打破自己从前的观念,找到“我长期以来一直想要相信的事物的证据,即我的头脑不仅是我需求和欲望的来源,也是能够抑制这些需求和欲望的图像的来源”。他试图从记忆中寻找那些碎片般却永恒的元素,透过玻璃窗“摇曳不定”的光线让他回忆起年轻时,自己如何喜欢盯着水彩调色板,“让每一种颜色都仿佛融入到它的名字里”。他写视线最远端的物体,似乎“在颤抖或躁动,直到令我产生错觉,好像有人在对我示意或向我眨眼”。他审视自己那些遥远的记忆,然后将他在内心构想的生活印刻在环绕于他周身的世界上,观察时间,观察空间。他认为,试图看到世界的本质是没有意义的,“你的思想不是让那块棱镜变得更神圣,就是变得更肮脏”。

“我的出版经历充满了各种起起伏伏、混沌困惑和错误的转折,而到了我生命最后的时刻,一切似乎终于开始好转了。”穆南本人曾在媒体采访中这样说。《边境地区》为穆南赢得了2018年的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被认为是他文学生涯中的最高成就,但直到《致读者的最后一封信》,他才真正为自己的文学生涯画上句号。用埃姆雷的话来说,这不是穆南最好的作品,却是一部必要的作品,“是他的人生,以及他在写作中呈现的人生版本唯一可能的结局”,“让我们从叙述者的声音中听到他自己生命的高潮,一个从物质身体的脆弱中脱离出来的,思想的生命”。《致读者的最后一封信》是穆南对自己之前14部书的回顾,汇成一个82岁作家的最后形象:“现在的我将如何评价过去的我?”需要指出的是,书名中的“读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而是穆南式写作的独特对象:一个“指导了我的大部分写作”的“理想读者”,一个“仅仅是她的存在就足以让他想到她过去和未来的无数种可能”的读者。他对她袒露心声:他实际上对学术性文学批评、书评家、哲学、神经科学、摄像机和出版商相当厌恶;他喜欢遵循句法规则的长句子,认为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赫尔曼·布罗赫(Hermann Broch)等人写了错误的长句;还有他的某种确信,“所谓 ‘时间’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是经历着一个又一个处所;而我们所说的记忆,并非一种往日重现,而是在无尽当下的某处首次上演的行为”。
 穆南新书《致读者的最后一封信》
穆南新书《致读者的最后一封信》
在消失的边缘
某种意义上,穆南一直处于“消失”的边缘,无论他的写作还是个人生活。1969年,和妻子凯瑟琳结婚三年后,他们共同搬到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郊区麦卡兰德,原因是从他童年生活过的本迪戈,到他的祖父家瓦南布尔,再到麦卡兰德,恰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形。2009年,妻子过世后,他搬到了维多利亚州更偏远的西部郊区戈洛克。因为假如把前面那个三角形按直角平分的话,那根分界线就直指他如今所在的戈洛克。“我很高兴,我的生命将在这根向量线中结束。”他曾在接受《悉尼先驱报》采访时这样说。除了对地理与几何的偏执,他还有一些在圈内一直流传的怪癖:没有嗅觉,讨厌大海,从来不戴墨镜,也从未坐过飞机——据说他在80多年的人生中,一步也没有走出过澳大利亚,只曾偶尔地坐车从维多利亚前往其他州。“每当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不是以矩形网格状排列的街道之中时,我就会变得困惑、苦恼。”这大概是一大原因。

很难说这样的穆南是现代生活的异类,还是典范——这个对电脑一窍不通,只会用右手食指在老式打字机上敲下自己所有作品的人,某种程度上俨然成为了今天的网络时代“原子人”的另类表征。而他所身处的这座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大陆都不相通的孤岛则成了他在这个世界最后的立足点,也因此成就了他作品中独特的“澳大利亚性”。就如库切对他的评价,穆南是那个澳大利亚“仍旧是英国的文化殖民地,仍旧压抑、清教徒式、对外国人充满怀疑态度”的时期,最后一代走向成熟的澳大利亚作家。尽管穆南的写作往往消解国度概念和地理指向性,但澳大利亚内陆平原的广袤和遥远以其鲜明的特质成为他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背景,而它的殖民主义历史则常常在一种碎片化、表现主义的回忆中变成一个简洁的博尔赫斯式寓言。他笔下的人物,就像他自己一样,似乎有着某种在非西方人中相当常见的感觉:从世界的中心——那些电影拍摄地、小说书写地、生命之轮运转地——被残酷地抽离了出来,但却仿佛乐在其中。
“我过着一些人口中所谓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不过,我更喜欢卡夫卡——我忘了是不是他——所说的, ‘如果你一直待在你自己的房间里,世界就会来到你面前,在地板上翻腾’。我来到了戈洛克,准备好了一直住下去,现在,世界已经在我面前翻腾起来。”穆南在戈洛克的家中这样告诉《纽约时报》,“学者、编辑、记者,他们都来登门拜访,看我怎样生活。”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降b小调
编辑:喜乐
图片:Getty、视觉中国
iWeekly周末画报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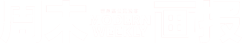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
© 2014 现代传播 Modern Media Co,Ltd.